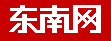林荷莲在陪党兴旺玩耍。
东南网5月7日讯(福建日报记者 张辉 通讯员 郑蔡乐 郭碧燕 文/图)“28、29、30!”4月20日,是4岁的脑瘫儿党兴旺来到林荷莲家中满月的日子。这一天,党兴旺给“妈妈”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。在例行的康复训练中,他可以连续站立30秒了。林荷莲兴奋地说:“刚抱回来的时候,他全身软绵绵的,连坐都坐不直。”
林荷莲在漳州市芗城区大同村居住了13年。一个月前,她与漳州市社会福利院签订寄养协议,将党兴旺寄养到家中。这是去年年底《家庭寄养管理办法》实施后,漳州市首例家庭寄养。事实上,家庭寄养早已开展多年,但林荷莲仍属少数派。这背后,是家庭寄养模式叫好不叫座的尴尬。
从院舍养育到家庭寄养
参与家庭寄养,林荷莲已不是头一回。早在去年2月,她就从漳州福利院接回了脑积水患儿党友平。半年后,党友平身体状况渐入佳境,被一个爱心家庭收养。在外人看来,林荷莲俨然吃力不讨好。她的“固执”源自一次在福利院的义工经历。
“一个大厅几十个孩子,只有五六个护工,根本照顾不过来,更别说陪他们玩耍了,小孩整天对着墙,个个愁眉苦脸。”震惊之余,林荷莲蹦出了这样的想法:如果能让这些孩子享受到家庭关怀就好了。
这和家庭寄养模式的初衷不谋而合。闽南师范大学副教授黄耀明长期关注漳州的特殊家庭。在他看来,传统院舍养育模式下,孩子缺乏依恋、信任和安全感,社会适应性差。家庭寄养可对症下药。“孩子进入家庭,重新建构家庭关系,有助于修复受损的情感,身心更加健全。”黄耀明说,在一对一的照顾下,孤残儿童的身体也更易恢复,生活自理能力得以提升。
2004年,国家出台了《家庭寄养管理暂行办法》。也就是这一年,福建各社会福利机构开始推行家庭寄养。由于缺乏家庭资源,漳州福利院直至2010年才开始这项工作。当年,该福利院请来了外援——长期开展家庭寄养服务的厦门市未来希望残疾人服务中心。很快,福利院的6个孩子分别进入了厦门、龙岩、漳州三地的5个家庭。
林荷莲参与到家庭寄养时,正值新法即将出台。相比暂行办法,新政进一步提高了寄养家庭的门槛。因此,林荷莲经历一番考验。
“福利院的孩子大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,对寄养者的能力要求高。”漳州福利院院长谢俊波表示,经过考察与评估,林荷莲具备了硬性条件:42岁的年纪正当年、初中以上文化水平、居住条件与家庭收入处于中等水平。更为重要的是,她在照顾特殊儿童方面经验丰富。
2003年,林荷莲6岁的小儿子患上癫痫。此后,她便开始全职照料病儿。经过康复训练,林荷莲成功让儿子从几乎瘫痪的状态重新站了起来。
此外,林荷莲居住的大同村距离福利院不过数百米,方便福利院进行后续的回访和跟踪。谢俊波还有进一步的构想:“在大同村培育多个寄养家庭,既便于集中管理,又能让家庭之间相互交流经验,也避免了周边对残疾儿童的歧视。”
除了硬件要求,谢俊波更为看重孩子是否能够融入新的家庭。“在进入新的家庭前,我们会让孩子和家长做前期融合,让家长每天来福利院抱抱孩子,以便孩子能够接受他们,避免今后因不适应而解除寄养关系,对孩子产生二次伤害。”他说。经过重重考验,今年3月20日,林荷莲把党兴旺抱回了家中。
资金掣肘,寄养家庭难寻
比起党友平,党兴旺的情况更为复杂——患有脑瘫和先天性心脏病。林荷莲照顾儿子的经验派上了用场。每天每隔一个多小时,她就要给党兴旺做一次站立训练。“最初让他扶着凳子站,可他害怕,我就用手搀着他,唱歌给他听,哄着他。”林荷莲说。在进行回访时,谢俊波惊奇于党兴旺的变化:“会站了,会打滚了,爱笑了,精神面貌好了,饭量都大了。”
欣慰之余,林荷莲也坦言,常有孤军奋战的无助感:“很多人投来异样的目光,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养个残疾儿,说我傻。”
目前,漳州福利院有孤残儿童70余人,但仅有6人进入寄养家庭,在漳州本地仅有2人。这个比例不可谓高。
“关爱孩子是人的天性,只是尚未形成家庭寄养的氛围。”在谢俊波看来,寄养家庭资源的匮乏,并不意味着社会爱心不足,而是由于宣传不到位,全社会对家庭寄养缺乏认知,加上传统观念对残障儿童心存芥蒂,以致这项工作难以为继。新政出台,提高了家庭遴选的标准,更加剧了家庭难寻的问题。
黄耀明则认为,更为直接的原因是激励机制不到位。“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远远高于机构养育,不能按照同等标准补贴。”黄耀明表示,经济激励与精神激励同等重要,他以“山东模式”为例,“不仅对寄养家庭经济倾斜,还优先评选为爱心家庭”。
然而,在我省,家庭寄养经费捉襟见肘。林荷莲说,自己每个月拿到手的补贴仅为1200元,其中1000元来自财政拨付给福利院的孤儿基本生活费,200元来自未来希望的资助。这对于月收入只有3000多元的家庭而言,徒增了经济压力。“买牛奶、钙片、纸尿裤、熬骨头汤,都要花钱,平常伤风感冒也只能自己贴钱。”林荷莲说,除非增加补贴,否则很少有人愿意参与其中。
南靖县60岁的老人黄荣财对此深有体会。2004年,他拾到弃婴党渠。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、癫痫、语言表达障碍等疾病。由于人员不足,县福利院与黄荣财签订了家庭寄养协议。由此,他也成为迄今南靖唯一的家庭寄养者。
“直到现在,她数数都数不到10,生活不能自理。”黄荣财说,自己靠种果树谋生,每个月收入2000余元。按规定,他每个月可以领到1500元补贴,但多年来,实际到手的不足1200元。往里贴钱,已成为常态。2010年,党渠接受心脏手术,扣除新农合报销部分后,老人自己仍花了1万余元。
“我们会督促福利院全额发放补贴,但即便如此也不够,家庭寄养不能总靠爱心维系,财政补贴标准应该提高了。”南靖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股长陈秋美说。
社会参与,才能养得更好
相比钱的问题,寄养者更关注孤残儿童的身心健康。“这些孩子大多有身体残疾,如果能从小就进行科学的康复训练,也许日后就能够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。”林荷莲说,虽然在寄养之初,福利院的专业康复人员对其进行了培训,但家庭条件有限,仍有赖于专业力量的参与。
“最初,福利院让我每天把孩子抱到福利院进行康复训练,但未能真正落实。”林荷莲表示,漳州福利院人手有限,五六个护理人员根本无暇顾及被寄养的孩子。她希望社会上能有一支专业的团队,来帮助党兴旺。
据了解,目前国内仅有宁夏、青岛、成都等少部分地方在家庭寄养集中区建立了专业的康复基地。在绝大多数地方,由于缺乏必要的医疗与康复条件,家庭难以承接重残儿童。尽管他们同样需要家庭关怀,但只能在福利院进行康复训练。
像党渠这样的孩子,则更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。陈秋美至今难忘第一次见到她的情形:“性格古怪,有时甚至打人、吐口水,不合群。”她说,孤残儿童往往自卑、孤独、社会适应性差,亟需心理干预。但目前,当地缺乏这样的专业力量。这也引发了黄荣财的忧虑:“我马上65岁了,按照政策,那时就要终结寄养关系,这孩子以后可怎么办呢?”
“家庭寄养的可持续性问题没有解决。”黄耀明说,家庭寄养不仅仅是把孩子送出去,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,“遴选一个家庭不难,但当他们碰到一系列的问题时该怎么办呢?比如医疗、心理、教育,未来的成长,都需要考虑”。
在黄耀明看来,社会力量的参与才是解决之道。“政府资源有限,让社会力量参与,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,同时又避免了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尴尬。”他说。
社会力量参与的方式便是政府购买社会服务。黄耀明设想,可尝试建立家庭寄养服务平台。这个服务平台由医疗、心理、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,负责寄养家庭的遴选、培训、跟踪、后续服务、监督等工作。“相当于是寄养家庭的加油站,遇到问题,可以寻求他们的帮助,借助他们的专业性,也能更好地帮助孩子进行康复和心理建设。”黄耀明说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