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织草席的老行当,如今只有几户人在坚持,希望“天宝草席”不会成为历史

这台木制机器就叫“席龟”,杨美珠把席草往里送,杨启成手握席扣,用力一拉,席草紧扣在席耕上

杨启成正在调整席耕的间距

杨美珠踩着纺耕车,正在制作席耕
东南网5月20日讯(海峡都市报记者 苏禹成 梁政 戴江海 文/图) 总有一些人偏执地爱着草席,一天的劳累后,在席草淡淡的香味中入眠,是幸福的味道。
漳州人说起草席,必定得说到“天宝草席”,喜爱它的人,会为它贴上各种标签:柔韧、透气、结实、耐用。
你知道吗?“天宝草席”并不是天宝镇产的,近日民俗专家郑德鸿走访村落,挖掘出“天宝草席”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。
在漳州南靖县靖城镇郑店村,曾经户户弄机杼,席草香满村。不过因为制作成本高,逐渐失去市场,如今仅剩几户人家还在坚持。
鼎盛时期 一天产300多张草席
席草散发着特殊的香味,一走进村子就能闻到
漳州南靖县靖城镇郑店村,位于九龙江西溪南岸,与天宝镇墨溪村隔江相望。
郑店村距离漳州市区约20公里,有村民2000多人。走进村口,并不像想象中那样,家家户户机杼轰鸣。如今,这里大多数村民都在栽培食用菌,沿着狭小的村道往村部走,两侧随处可见蘑菇房。
家家户户做草席的情景,虽然距今已有10多年,不过,现在随便找出一个村里人,还能讲得头头是道,这似乎是属于村庄的荣耀。
老郑说,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,夫妻搭档,几乎每家都是草席作坊。制作草席的两种主要原材料:席草和席耕,也是由村里自行生产制作。“席草一年两季,初夏、秋天可以收割,席草会散发特殊的香味,当时一走进村子就能闻到。”老郑称,高峰时期,村子一天可以生产300多张草席。
郑店村产的草席被船运到天宝镇上,销售到各地。由此造就出“天宝草席”的盛名。
午后瓦房 夫妻搭档札札弄机杼
不仅是增加收入的手段,也是对过往生活的延续
大多数年轻人已不再制作草席,只剩一些老人还在坚持,对他们而言,这不仅是增加收入的手段,而且是对过往生活的延续。
杨美珠70岁,她的丈夫杨启成73岁,夫妻俩从10多岁开始制作草席,所有工序都驾轻就熟。
午后的瓦房,光线不算充足,这是他们经营的小卖部,也是一个草席作坊。杨美珠双脚踩在纺耕车上,如蹬脚踏车一般,缓缓转动滚轮。她一手挑来黄麻丝,一手将黄麻丝轻轻卷动,揉编成一条,往纺耕车上送,经纺耕车上横梁一转,成了结实的席耕。
一张草席中,纵向分布的是席耕,横向分布的是席草。根据草席的尺寸,席耕被固定在“席龟”上,“席龟”是一种用木头做成的支架,席耕按照一定的间隙罗列在上面,方便席草穿梭其中。
接下来,杨启成上场了,他端来一罐花生油,用刷子沾上一点,刷在席耕上,让席耕保持柔韧。杨美珠一手握竹签,一手抓起席草,把席草的一头钩在竹签上,往“席龟”上送。在席草与席耕交错后,杨启成握紧“席龟”上的席扣,用力往下一拉,将席草紧扣在席耕上。
要完成一条草席,这样的工序,要重复上百遍。“一张长1.2米、宽0.5米的草席,夫妻俩要整整做一个下午。”杨美珠称。
后继无人 因成本高失去市场
不久后,“天宝草席”这个地域特色,或将成为历史
据漳州民俗专家郑德鸿称,南靖县靖城镇下魏村,才是“天宝草席”的最初原产地。下魏村与郑店村相邻,距天宝镇只有约3公里,隔江相望。
下魏村编织草席历史悠久,且其工艺一直保密,但到上世纪60年代,因社会动荡,传统观念被打破,加之当时农村经济几乎崩溃,如果能做手工赚钱,可解燃眉之急,郑店村与下魏村通婚的一些家庭,便开始学做草席,并很快形成规模。
由于做草席劳动强度大、成本高,一张1.5米左右的草席售价150元以上才能赚钱,在上世纪90年代后逐渐失去市场。现在郑店村仅剩下几户老年人在织草席,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。
郑德鸿说,也许再过不久,郑店的草席将会消失,“天宝草席”这一个具有地域特色的漳州名产,也将成为历史。 |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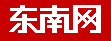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6e17fc48-9d69-405f-a2a6-e4a23f614333.png)
3623b05a-05a8-4a4b-b23f-00eab99fe03d.png)
e36f32bf-804d-4725-b640-26561e53f2fe.png)
5095e6cd-29e8-438e-9a7b-72cf85705bd9.png)
a9ee54ed-dd65-45bb-8026-37ed1771a334.png)
9be162b3-8527-443a-9631-ea67042584e8.png)